尋找轉型正義原則
- 謝世民
- Nov 6, 2018
- 6 min read
柯文哲市長日前在與婦聯會主委雷倩的座談會中,引述他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波蘭總統華勒沙交流的經驗,並表示:「轉型正義,第一是解決現在的問題,第二是預防以後再發生,第三才是追究後續責任,如果把順序倒過來,那就搞不完。」
柯市長的這番談話,似乎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因為我們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刻在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我們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在徵集「威權統治時期,政府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蒐集、製作或建立之政治檔案」,並準備「邀集各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柯市長的這番談話似乎蘊含說,這兩個委員會的這些作為,恰好背離了落實轉型正義應當謹守的「順序」。
從輿論界的反應來觀察,柯市長的這個觀點,讚賞者有之,但人數似乎不多(國民黨懷疑他動機不良,意在爭取泛藍選民的支持),遠遠少於撻伐者。這個結果可能讓柯市長大驚,因此他隔天深夜便在臉書上公開澄清,表示自己對轉型正義的認識有限,犯了過度推論的謬誤,同時也承認「解決現在的問題、撫平受害者的傷痛、避免未來再犯、追究過去的責任歸屬,同樣重要。」
柯市長的澄清,就內容而言,只是一般性原則的陳述,不再影射特定的制度和政府作為,這應該有助於降低批評者對他的攻擊,增加他順利連任的機會,但一點都無助於我們想清楚轉型正義所涉及的各種難題。
就我所見,在這些難題中,有一個我們必須去思考、但長期被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是:
就台灣社會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就台灣社會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圖片來源:行政院網站
這是正義問題。正義問題不是私人問題:雖然思想自由是我們基本權利,但正義問題並不是每一個人「愛怎麼想就怎麼想」、「沒有正確性可言」的問題。正義問題也不是分散性的問題:其答案不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援引自己確信正確的原則作為判斷之依據」。正義問題的特徵之一,在於它的公共合理性,這意思是說:
正義與否,每一個人只能依據「大家都不能合理拒絕作為共同公開援引的原則」來判斷。
正義問題之所以具有這個特徵,乃是因為國家在必要時可以強制貫徹正義的制度,而如果制度的正義性無法建立在大家都不能合理拒絕的原則上,那麼,強制貫徹之道德正當性對某些人而言,就顯然不足。強制,並不依賴於受強制者的實際同意才具有正當性(一個人是否實際上同意,牽涉太多偶然因素,規範效力的範圍有限),但必須是受強制者沒有充分理由拒絕的原則所允許的,否則就不夠尊重(作為目的自身)的受強制者。根據美國哲學家 Charles Larmore 的研究,這套「正當強制論」是當代自由主義正義觀的道德基礎。
如果這套正當強制論對我們具有理論吸引力、如果我們也認為,正義問題的特徵之一,就在於它的公共合理性,那麼,回到我們在台灣思考轉型正義的具體脈絡,關鍵的問題當然是:要評斷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是否正義,什麼原則是「大家都不能合理拒絕作為共同公開援引的原則」呢?
明顯地,這是一個高度抽象的問題,可能很難一下看到有什麼備選的答案。不過,熟悉羅爾斯《正義論》的朋友應該會想到:我們也許可以在他的「原初狀態」裡找到答案。
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是一個社會成員共同選擇正義原則的假想場域,其諸多設定條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大家必須隔著無知之幕去做選擇(不知道任何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資訊,例如性別、家庭的社經階層、天生的資質禀賦、價值觀或宗教信仰等等)。羅爾斯主張,無知之幕的設計,足以保證我們在公平的情境下去選擇正義原則,而他也認為,他的正義論賦予「公平」的重要性也契合我們深思熟慮之後的道德判斷。

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是一個社會成員共同選擇正義原則的假想場域,其諸多設定條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大家必須隔著無知之幕去做選擇。圖片來源:The Veil Of Ignorance, BBC4 Youtube頻道截圖
雖然羅爾斯的《正義論》並沒有討論轉型正義問題,不過,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不公平,當然是任何人可以援引作為拒絕一項正義原則備案的充分理由。這個觀察,如果成立,那麼,「回到羅爾斯公平的原初狀態」,當然就是一種尋找轉型正義原則的好方法。因此,我們可以不必再問:要評斷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是否正義,什麼原則是「大家都不能合理拒絕作為共同公開援引的原則」?我們現在必須問的是:要評斷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是否正義,什麼是我們在原初狀態中、隔著無知之幕會選擇的原則呢?
這個羅爾斯式的問題,我們必須分兩個步驟來回答:第一步很簡單,第二步比較複雜。簡單的回答來自羅爾斯的「正義第一原則」。羅爾斯論證說,在原初狀態中,我們會選擇「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原則」,並會同意這項原則具有優先性,接著也會去選擇、設計一部能有效落實「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的憲法。
就羅爾斯正義第一原則而言,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憲法,都是正義的憲法。顯然地,如果「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是最優先的正義第一原則,那麼,我們在原初狀態中當然就要同意說,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不得違反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包括了一般所謂的「法治國原則」)的正義憲法。
比較複雜的第二步,來自於第一步的答案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可能不違反?」。因為旨在實現「轉型正義」的必要制度和措施,無論如何小心設計,似乎難免會抵觸正義憲法對立法所設下的許多原則性的限制。就以我們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而言,其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似乎就違反了正義憲法中多項的「法治國原則」(例如,「法安定性原則」、「禁止個案立法」、「法明確性原則」、「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然而,對《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支持者而言,那些為了實現轉型正義的必要制度和措施,必然是正義憲法所容許的;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在羅爾斯的原初狀態中會選擇的正義憲法並不會禁止《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會陷入這個爭議,乃是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到,針對具體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我們在羅爾斯的原初狀態中,其實並沒有基礎去選擇什麼樣的一部憲法:不論是明確禁止《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憲法,或是明確允許《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憲法。不過,我們可以適度地修正羅爾斯對原初狀態的設定,來解決轉型正義原則的選擇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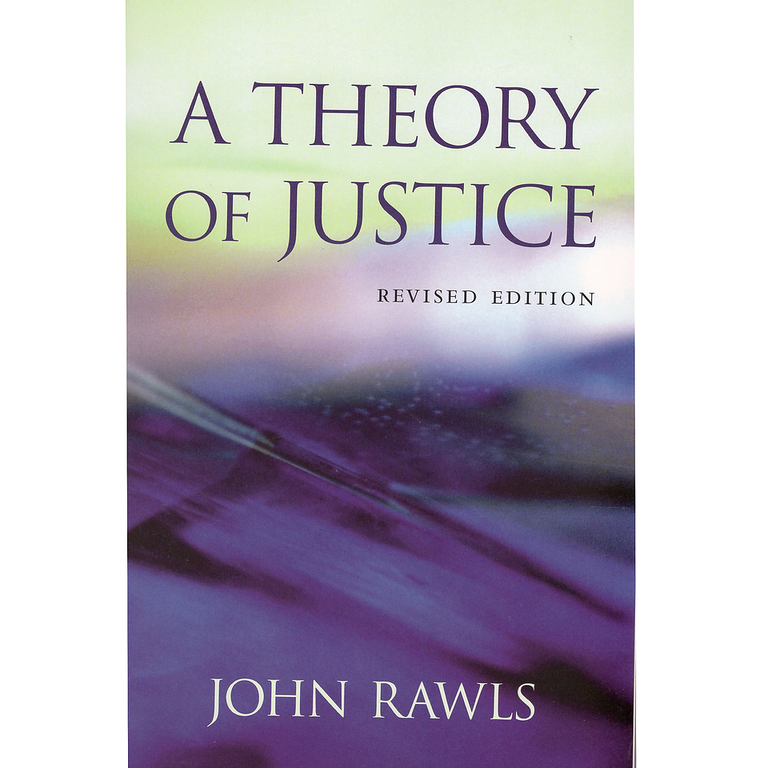
雖然羅爾斯的《正義論》並沒有討論轉型正義問題,不過,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不公平,當然是任何人可以援引作為拒絕一項正義原則備案的充分理由。
在修正的原初狀態中,我們知道,我們已經選擇了一部正義的憲法,而且我們也接受本國實踐正義憲法的基本模式:一般而言,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在沒有被司法機關宣告違憲之前,仍然有效,政府必要時可以強制貫徹這樣的法律。我們還知道,為了實現轉型正義的制度和措施(例如《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這類的法律),其合憲性往往是合理爭議的對象。
不過,我們隔著無知之幕: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政黨是否繼承了威權統治時期的不當財產,因此,我們會希望,萬一自己的政黨繼承了不當財產,立法機關通過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必須是合憲的,不僅如此,為了避免財產遭受違憲法律侵害的風險,我們還會希望,在政府強制貫徹《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前,《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合憲性是己經獲得確認的。這些考慮,綜合起來,充分支持我所謂的「合憲性確認原則」: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侵害人權、執政黨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措施,必須在獲得「合憲性確認」後,始得實行。
借用羅爾斯的術語來說:「合憲性確認原則」是我們在原初狀態中、隔著無知之幕會選擇的一項轉型正義原則。或者,以政治自由主義的典型論述方式來說:「合憲性確認原則」是一項大家都不能合理拒絕的轉型正義原則。
作者為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