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風之帝國》
- 聯經出版
- Mar 12, 2021
- 15 min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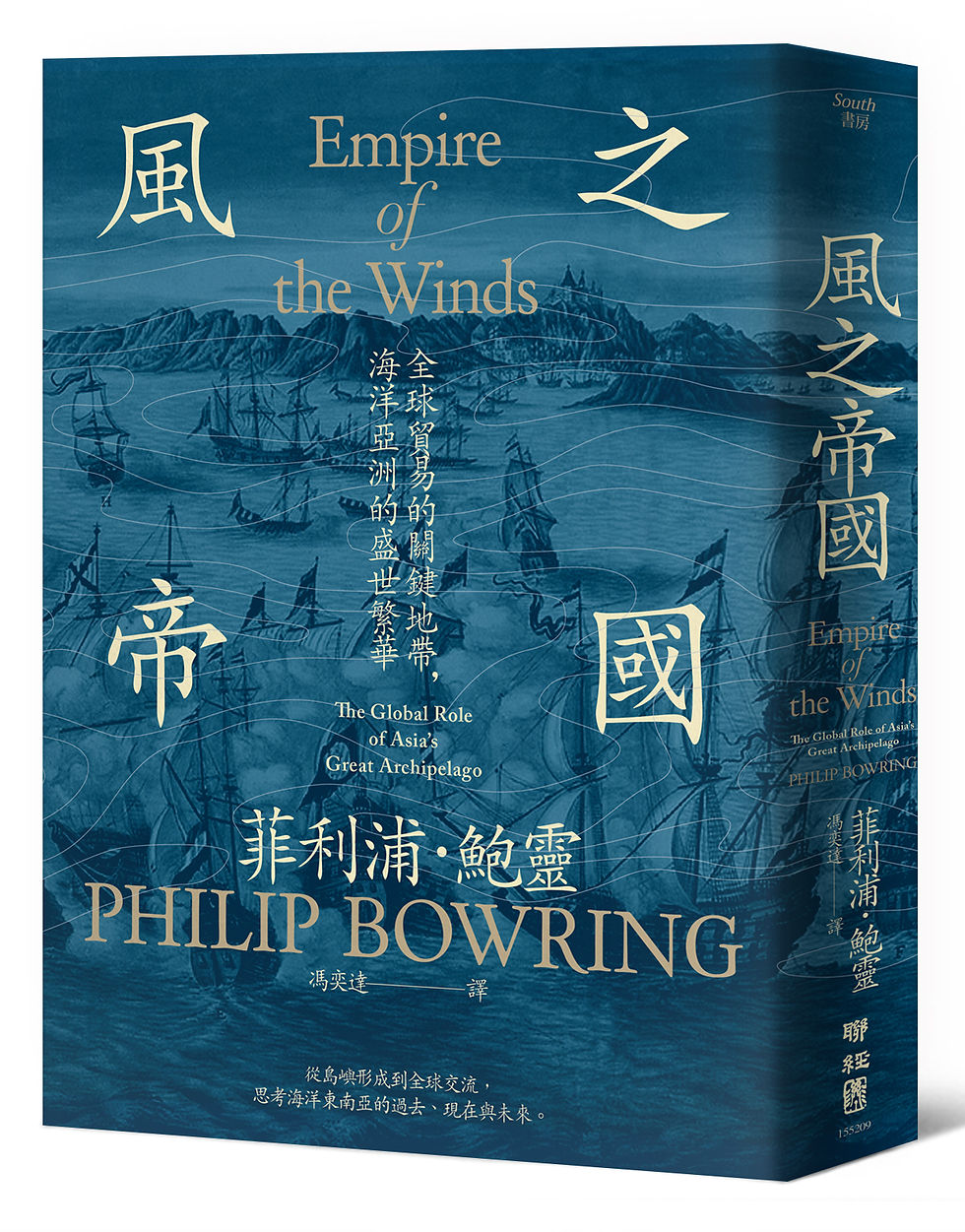
第五章 文化來自印度,商品來自中國
最早提供文字記載讓人一窺努山塔里亞的或許是中國,但法顯時代的中國與當地的接觸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努山塔里亞與印度已有大規模的貿易和交流,為這個區域帶來人們所說的「印度化」。這個詞稍嫌誇大,但印度文化影響力滲透東南亞島群與大陸的程度確實毋庸置疑。
泰國灣(Gulf of Thailand)的考三玉(Khao Sam Kaeo)發現了年代約西元前三○○年的印度陶器,越南也有來自沙黃文化時期、源自印度的文物出土。到了西元初期,印度跨安達曼海至馬來半島北端數個地點(接近今日的拉廊[Ranong])的定期貿易已經相當明顯。已經有人找到羅馬與印度器物、大量陶器和若干泰米爾語銘文。錫含量高的青銅器也有出現。過去認為這些是當地製作的青銅器,畢竟相較於印度,當地有豐富的錫礦供應。但後來的研究指出這些器物來自印度。跨安達曼海的錫貿易很可能已經存在,為印度金屬匠提供原料。
在不同時代,馬來半島的安達曼海與泰國灣兩側同時有許多地方扮演轉運站的角色。早期與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進行貿易時,用的是比較偏北的路線,西岸的吉打逐漸愈來愈重要。西元三世紀的泰米爾文學已經有提到吉打。泰米爾商人偏好的路線可能就是吉打,至於孟加拉商人則是走比吉打更北的路線,跨越克拉地峽前往扶南。
我們並不清楚印度宗教、文字、藝術與政治制度在這個區域生根的過程,但結果很容易看到。上述的過程相當漫長,而且相當平和(只有朱羅王朝在十一世紀擴張到馬來半島時例外),是以貿易為動力,同時也帶來宗教與其他思想。早在二世紀時,扶南便已採用源於印度的文字,當地也有婆羅門的蹤跡。近年來,考古研究同樣在馬來半島西岸的雙溪峇都(SungeiBatu),找到口岸與城市聚落存在的證據,不僅有佛教器物,還有製鐵活動。該口岸的年代早至二世紀,而且很可能是扶南貿易體系的一環。
建國神話
來自印度的人將貿易與宗教帶到農漁業早已興盛的扶南地區,而地方勢力若非與之合作,就是受其扶植。扶南國就帶有這種痕跡。根據後來的中文史料,扶南國成立於西元一世紀,是由名叫混填(Kaudinya)的南印度婆羅門商人與當地公主結盟而成立的國家。公主的軍隊試圖抓住混填,但混填堅決抵抗,後來雙方成親。根據地方傳說,公主是水神的女兒,住在某座山上,而混填喝了這裡的水。這段傳說或許可以詮釋成當地的王族主宰了來往船隻,而混填則帶來灌溉技術,創造了扶南的運河。該地區亦有其他扶南類似的建國神話。就扶南的例子來說,其建國神話暗示著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商人與地方統治家族合作、聯姻,帶來教師與文字。類似的建國神話在該地區層出不窮。無論歷史真相為何,這些神話描繪出的都是從事商業,對海外人口、制度與宗教抱持開放的社會—以扶南而言,所謂的「海外」,就是政治結構與科技發展更先進的印度。
地方統治者引進印度習俗,作為強化自身權利的手段。他們利用王權制度,與神職人員結盟,結合宗教儀軌,從而將權力結構制度化,從仰賴個人力量、常常轉瞬即逝的政治實體發展為王朝。這並非突然發生的轉變,而且可能要到西元四○○年前後,印度文化的影響力才超出港口地帶,各國也才開始運用印度曆法,將印度字彙加進日常用語中。
印度文化與政治思想也透過洞里薩湖(Tonle Sap),漸漸沿湄公河而上,傳到今天柬埔寨與泰國昭披耶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印度對馬來半島的影響力之所以更強,是因為印度商人主導了此地對西的貿易,至於對東的貿易則掌握在努山塔里亞手中。到了西元三○○年前後,印度的文化影響力抵達越南海岸,沙黃文化朝印度化的方向演進後,幾個占人的國家於焉成形。
在整個西元第一千年期,印度文化與經濟影響力都是整個海洋東南亞與大半個大陸東南亞的主導力量。中國本身鮮少有直接影響。若從中國後來扮演的區域角色,尤其是從華人離散來看,這件事挺讓人難以理解。其原因包括中國很晚才發展出越洋船隻;中國書寫體系相當複雜;相較於印度教與佛教教誨,儒家學說可能缺乏文化可移植性;中國人戰略思考以北方、陸地為取向;以及相較於印度海岸地區的商人與努山塔里亞船員,中國人缺乏對外貿易的經驗。運送中國商品一事固然是貿易的催化劑,但運送這些商品的人卻不是中國人。
印度人本身主導印度化的推動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只能推測。二十世紀中葉,印度歷史學家R.C.瑪朱穆德(R.C. Majumdar)在著作中主張有大量的印度人到這個地區殖民—婆羅門、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人在整個地區建立統治群體,取代本地領導人,將完整的文化與王權體系帶進落後的南島與高棉政治實體。研究該地區的法國歷史學家喬治.賽代斯(Georges Coedès)則把瑪朱穆德的理論修改得較為溫和,主張婆羅門是主要的推手,採用的手段包括直接統治、與當地統治者為互利而結盟、與地方菁英聯姻等。
近年來,學界傾向於把來自印度的個人或團體的重要性下修,轉而視印度化為多半出於自發的過程,推動印度化的地方領導人本身採納了他們認為更先進的理念、階級與王朝體系,以強化自己的地位。因此,這個地區吸收印度文化與科技的方式,基本上與日本吸收中國文化,以及地中海周邊國家吸收希臘文化的方式如出一轍。海岸小國的統治者為貿易而競爭,他們需要改善自己的行政制度,截長補短,與自己的造船和航海專業般配。
史書因為缺乏實證之故而壓縮印度化過程的時間,但這其實是一段歷時數百年的漸進過程,且同時有來自北印度與南印度的影響。早期的印度影響力主要來自北印度,經孟加拉而來。但半島地區與印度南方的泰米爾地區,以及與信奉佛教的斯里蘭卡之間的關係也益發重要。早在西元二世紀,泰米爾文獻就有與爪哇大量貿易的證據。一份西元三世紀的泰米爾語碑文在泰國出土,暗示泰米爾商人或許已在此定居。當時,許多泰米爾人與僧伽羅人(Sinhalese)都信奉佛教。來自南印度的帕拉瓦文字(Pallawa script)成為寮國、高棉、爪哇與峇里文字的基礎。據說,帕拉瓦文字的圓滑形狀尤其適合書寫於棕櫚葉—直到十七世紀左右,棕櫚葉都是印度與東南亞大部分地區所使用的書寫材料。
朝聖之路
印度文化傳到爪哇的時間,比馬來半島和大陸東南亞來得晚,印度教的傳入也先於佛教的教誨更早。婆羅門信仰先傳播到當地,接著才是佛教。五世紀的中國佛教僧人法顯曾提到佛教傳播速度之慢。他發現在耶婆提(爪哇):「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
法顯對於從斯里蘭卡出發的航程有生動的描繪,他搭乘的大船「可有二百餘人,後繫一小舶,海行艱嶮,以備大舶毀壞」。兩天後颳起一場風暴,大船開始漏水。船上的商人大駭,想換乘小船,但小船船員卻將繩索砍斷。大風吹了十三個晝夜。一行人終於在一座小島靠岸,修復船隻,後來又花了九十天才抵達耶婆提。從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這艘船從斯里蘭卡出航後並非直接取道巽他海峽前往耶婆提,而是走正東方通過馬六甲海峽,卻在途中被孟加拉灣的暴風往北吹,很可能是在安達曼群島觸陸。最後,船乘著東北風,穿過海盜騷擾的海峽,抵達耶婆提。
法顯為了等待風向轉變,從西元四一二年至四一三年間等了六個月。他返國之路甚至比從斯里蘭卡出發的這一程更危險。五月時,法顯搭的船趁西南季風剛起時,帶足航程預估所需的四十天給養,前往廣州。但船卻遭到剛形成的颱風所侵襲—這陣風想必把船吹到台灣東方海面—此後轉往西北又航行八十天,才終於在山東登陸,跟原本的目的地差了兩千公里。從斯里蘭卡出發的這整趟行程花了將近一年,有時候相當危險,但過程中卻也長期無事可做,還得忍受夏季的酷熱,畢竟微弱甚至反向的風會讓行船的速度非常緩慢。他的經歷描繪出往東北方航行之危險,尤其不時會遭遇狂暴的西南風。入夏後,一旦來到北緯十五度左右,船隻就有可能遭遇颱風。颱風通常在七至九月形成,因此一旦吹起西南風,就必須馬上出發。
法顯此行的時間,是在佛教大舉傳入爪哇之前不久。五世紀時,訶陵(Holing,可能位於爪哇的三寶瓏[Semarang]附近)派使節前往中國。根據中文佛教典籍,三寶瓏改信佛教的推手,是名叫求那跋摩(Gunavarman,「跋摩」[varman]是君主的頭銜)的北印度王子與傳教者。求那跋摩在四二四年抵達三寶瓏,停留多年,成為國王的策士,不僅助其擴張,也建立自己身為佛教火炬的名聲。不過,當地改信佛教之前,流行的應該是印度教,而非更早的傳統信仰。史書的記載並不明確。求那跋摩名聲響亮,據說中國皇帝因此邀請他前來弘法。得風力之助,求那跋摩搭乘的商船並未在原先預計的「一小國」(可能是占婆,或是婆羅洲西北的某個地方)中途停留,而是直接抵達中國。求那跋摩此行一帆風順。
法顯與求那跋摩的海上經驗大相逕庭,但兩人的敘述皆顯示船隻經常直接從蘇門答臘或爪哇航行至中國,頂多在途中的占婆或婆羅洲海岸停靠。法顯也指出印度作為佛教泉源的核心地位。據他說,印度是「聖地」,中國則是「邊地」。
爪哇當地證明印度影響的最早物證,也來自五世紀。雅加達附近出土的碑文歌頌信奉印度教的君主普納跋摩(Purnavarman),他不僅開疆闢土,也重視貿易發展,擴大大魯河(Tarum River)河口的口岸,也就是他的首都—都固(Tugu)。普納跋摩的塔魯瑪迦(Tarumnegara)王國可以回溯到四世紀中葉。與其他國家類似,塔魯瑪迦據說也是因為來自印度的商人與當地公主聯姻而立國。普納跋摩顯然是位非常有成就的君主,西爪哇與中爪哇許多小國君紛紛歸順於他。茂物(Bogor,雅加達南方)出土的梵文與帕拉瓦文碑文記錄著這位國王的豐功偉業,包括修築排水道、防洪運河與眾多廟宇。銘文之一寫道:
這位以忠實執行其職責與舉世無雙而知名的國王,名為尊貴的普納跋摩,統治著塔魯瑪(Taruma)。敵人的箭矢無法射穿他的甲冑。他歷來皆能成功摧毀敵人的堡壘,以尊榮接納忠心於他、痛恨其敵人之人。
爪哇的國際色彩比較濃厚,這解釋了中國佛教徒為何會前往斯里蘭卡等地朝聖,而非爪哇。印有佛教符號錢幣與封戳,證明佛教在貨幣經濟進入各島嶼時發揮的影響力。在爪哇,佛教於六世紀時達到高峰,之後印度教則強勢復興,這個現象可能反映了印度教在笈多王朝時代的早期復興。不過,佛教在爪哇的影響力依舊強大。
七世紀晚期,中國僧人義淨提到末羅瑜(Melayu,今蘇門答臘占碑[Jambi])有上千名佛教徒。蘇門答臘是佛教學術中心。義淨不只談及自己的經驗,也提到其他中國僧人走訪印度的經驗。他對行程的時間點與需時提供了可貴的描述。義淨從廣州乘船出發,直接前往室利佛逝,之後再到末羅瑜。在蘇門答臘待了八個月之後,他順著西南季風前往吉打。等到吹起東北季風,他又搭了六天的船,抵達尼科巴群島(Nicobar Islands),接著花兩週時間抵達西孟加拉胡格利河河口的塔姆盧克(Tamluk),靠近今日的喀爾加達(Kolkata)不遠。回程時,他花了兩個月時間直接前往吉打,接著搭乘一艘室利佛逝船,趁著東北季風續至末羅瑜,在當地等到西南風吹起,然後搭了將近一個月的船回到廣州。
日子一久,印度教與佛教皆得益於信徒的贈地。寺廟與僧人、祭司社群在王族的支持下逐漸擴張,成為工藝與宗教藝術的中心。然而,地方上對於印度思想的接受仍然有選擇性。比方說,儘管各個社會隨著財富與文化的增長而愈來愈階級化,但人們從未接受印度的種姓制度。綜觀整個地區,努山塔里亞女性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皆比印度更為活躍,而且古今皆然。峇里式印度教向來展現出與印度的印度教不同的特質,畢竟外來的宗教會根據當地既有的信仰與習俗而自我調整。努山塔里亞借來文字與許多字彙,但外來語言從未取代各式各樣的南島語言。
儘管從印度與中國到爪哇與蘇門答臘興起了直接的聯繫,地峽貿易仍然有其重要性,能連結印度東部與孟人(Mon)、暹羅人與高棉人居住的大陸東南亞。貿易同樣帶來了佛教—佛教同時與印度教和地方古老信仰相爭,但前兩者的影響範圍恐怕仍局限於宮廷和附近的城鎮。佛教也激勵了信徒乘船,僧人乘船弘法。
印度的文化影響力憑藉貿易,維持了好幾個世紀。不過影響力雖巨,卻不見得在各地都很深刻。中國的影響力(有時候則是統治)在占婆以北最為突出。今天越南盛行的佛教其實源於中國,而非直接從印度或斯里蘭卡抵達當地的。有鑑於儒家思想在越南與中國的地位,佛教從未與這兩國的君主體制建立如其他地方那樣的緊密關係。
印度的影響力愈往東邊也就愈小。民答那峨島、宿霧島、呂宋島、蘇拉威西島與巽他海諸島雖然地處偏遠,卻始終是區域貿易體系的一環。來自印度的文字體系逐漸為當地所用,某些梵語詞彙也連同借用過來。一張刻有銘文的九世紀銅盤在馬尼拉出土。民答那峨東北部的城市布湍早期是跟印度,後來則跟中國有貿易往來。布湍出土的金質文物展現出來自爪哇的印度教—佛教影響,以及高度的冶金與工藝水準。印度商人造訪蘇拉威西,在當地可能也有小型聚落,但他們對當地明確的文化影響,只限於部分的火葬習俗遭到取代而已。整體而言,印度對努山塔里亞東部與北部島嶼的影響,並未跨出傳統上位於海岸的貿易地點。
文字體系與國王
至於其他領域,人們對印度思想的接受同樣有所選擇,而非全盤採納。他們固然借用文字體系,在年代最早的本地書寫中使用印度的詞彙,但無論是宮廷或平民,言談仍維持當地的南島語或高棉語。梵語或許一度有相當的宗教與行政地位,有如拉丁文在中世紀歐洲的角色。但當地語言的書寫漸漸採用印度的帕拉瓦文字,目前最古老的古馬來語文獻可回溯到七世紀的蘇門答臘,就是帕拉瓦文字寫成的。我們在八世紀時看到卡維文字(Kawi script)的發展—這種文字演化自帕拉瓦語,用來書寫古爪哇語。
這種文字成為其他文字的基礎,包括後來的爪哇文與峇里文,而且至今仍在使用。最早的高棉語書寫,同樣來自七世紀,使用的則是調整過的帕拉瓦文。六百年後,這種調整過的文字成為泰語書寫的基礎。印度語言影響力的來源也很多元。進入爪哇早期書寫的,只有來自宗教語經典文獻中的梵語詞彙,而沒有普拉克里特語(Prakrit,即印度平民的語言),但泰米爾語詞彙卻出現在蘇門答臘。儘管引進了印度宗教,但社會結構看來還是維持本土的樣貌。各個海洋文化借用了印度的藝術與建築理念,但加以調整,產生獨一無二、一望便知的特色。
宗教與文字之外,印度最大的影響體現在司法與行政議題上。統治菁英廣泛研讀印度的治國寶典《政事論》(Arthashastra)與古代婆羅門法典《摩奴法論》(Manusmriti),兩書對政府體系的發展有絕大的影響力。《政事論》成書於西元四世紀,是以北印度為核心的孔雀王朝時期。孔雀王朝據說信奉愛好和平的耆那教,但《政事論》卻要求統治者必須無情保護國家利益,而且要有紀律、認真而有學識。這是一帖開給開明專制的世俗藥方,信奉任何宗教的統治者皆能服用。
印度教的神聖王權觀念尤其吸引統治者,畢竟這能讓權力的行使看起來比個人領導更為崇高:權力來自天授。另一方面,佛教(與耆那教)更能同理商人利益與財富累積。信奉佛教的人也更不受種姓因素與宗教儀式所限制—對於長期身在海上的人來說,宗教儀軌是種困難。
中國的魅力
中國逐漸經由貿易與朝聖,意識到自己的南方鄰居,但相關認知依舊欠缺而含混。西元五世紀早期,島群與中國、與印度之間已有直接貿易。陸路仍有使用,但相對衰頹。對中國的貿易海路在五世紀時起飛,一部分是因為通往西方的陸路封閉了,一部分則是因為透過海路直接聯繫,可以免去跨馬來半島的轉運。努山塔里亞人試圖以派遣使節的方式,促進與中國的貿易。
五世紀成為所謂「朝貢體系」的起點。西元四三○年至四七三年間,紀錄有案的朝貢使團就有二十個,共來自五個不同的島嶼與半島國家。統治者進貢中國,期待本國商人能得到歡迎。其中一國奉表陳情:
臣國先時人眾殷盛[……]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並市易往反,不為禁閉[……]願勑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這段文字暗示了:第一,貿易口岸彼此的競爭關係;第二,最弱小的口岸必須設法取悅中國;第三,外國商人有可能在廣州遭到勒索;第四,使團(至少就努山塔里亞人的角度來看)有助於獲得正面的貿易待遇。
對中國人來說,納貢則帶有紆尊降貴的成分。總之,根據中文史料所載,干陀利(中國早期對室利佛逝的稱呼,但也可能是占碑)統治者在西元五○二年做了個夢,夢中有一佛教僧人建議他:
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
所謂的「聖主」,指的是梁武帝—這位虔誠的佛弟子在中國南方建立了梁朝,統治達四十七年。武帝不僅茹素,而且禁止用動物祭獻。
貿易的內容也在增加。中文文獻提到衣物、薑黃與檀香,可能全來自印度;來自波斯或阿拉伯的乳香;此外還有來自蘇門答臘或馬來半島的樟腦、安息香(一種同樣可以入藥用的芳香樹脂)與沉香,並提到「香水與藥」。貢品必然小巧而高價,但貿易商品則會有布疋、瓷器與金屬等大體積的貨物。
貿易持續成長,甚至連高棉人在六世紀早期征服扶南,且其他口岸取而代之之後也依然興盛。位於馬來半島北大年附近的狼牙脩國,繁榮的程度已足以在西元五一五年遣使中國。中文文獻提到該國國王與貴族「以金繩為絡帶,金鐶貫耳,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
七世紀初,一名中國使節提到狼牙脩的國王,是其父王遜位成為僧侶時所指定為王的。國王有三名妻子,全都是鄰國國王的女兒。王宮有兩層樓,所有的門都面向北方,王座也是。國內有各種大臣管理。他還提到源於印度教的婚禮與葬禮儀式。婆羅門來到當地,多半是為了賺錢,而非傳道。另一位中國訪客提到「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這是個印度教國家,其獨立地位維持到七世紀晚期,和吉打在同一時間落入室利佛逝的勢力範圍。
另一個因跨地峽貿易而興盛的小國是沙廷帕(Satingpra),靠近宋卡(Songkhla,亦拼作Singora,是Singapura的簡稱,馬來語意為「獅城」,字源為梵語),介於大海與宋卡湖(ThaleLuang)之間。宋卡湖潟湖,座落在地峽的狹窄處,提供通往安達曼海的通路。「沙廷帕」之名來自孟語—高棉語的「stung」(河流)與梵語的「pura」(城市),該國一度處於孟人的陀羅缽地王國(Dvarati Kingdom,橫跨今天部分的泰國與緬甸)支配之下。當地出土大量的中國陶器、較少的波斯與阿拉伯陶器(不過本地亦有窯爐),以及佛教和印度教青銅像與石像,顯示其在七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的重要貿易地位。據中國史料所言,沙廷帕發展非常興盛,但直到最近才有空照圖可以佐證。
除了貿易,沙廷帕的運河網絡不僅能支撐稻米種植,更意味著能將物品運輸到山區,若從此跨越到安達曼海岸的董里(Trang),路程也就更短。董里是地峽東岸數個貿易口岸之一,其重要性足以引起室利佛逝與中國的興趣。從西岸的達瓜巴(Takua-pa)前往董里北方的口岸蘭佛(Laem Pho,靠近素叻他尼),距離也很短。根據阿拉伯與中國史料,十世紀時,許多意欲前往中國的阿拉伯商人都會利用這條半島路線。他們泰半是搭乘泰米爾船隻來到半島。隨著時間過去,海水退去,幾個地峽口岸的重要性也因地理形勢改變而終結。某些地方在今天的海岸線,比九世紀時候後退了三公里遠,與印度的貿易交流因此衰頹。
不過,印度的文化影響力早已在超過一千年的時間中,強化了各個努山塔里亞國家之間的聯繫—無論是位於爪哇、蘇門答臘還是馬來半島—甚至還觸及島群的東部與北部。既有的貿易活動在海洋環境與古代文化的相似性上,又增添了共同的宗教思想與王朝體系,進而帶來大國實體的形成,以及因王朝聯姻而湧現的情誼(與敵對關係)。這幾股力量將在不久後凝聚,形成歷來世上最成功的其中一個貿易帝國。但一切的背後都少不了貿易與利益的吸引力,涉及許多地區的物產與需求,其中又以中國最為重要。不過,貿易活動本身主要仍掌握在努山塔里亞、印度人與其他非中國人手中。室利佛逝的悠久歷史即為明證。
作者為記者兼作家,自1973年起便活躍於亞洲。曾任《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總編輯,也是《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與《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特派員,《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專欄作家,並為《衛報》(Guardian)與《南華早報》供稿。畢業於劍橋大學歷史系,研究亞洲海洋歷史與經濟。
書名:《風之帝國》
作者:菲利普.鮑靈(Philip Bowring)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1年2月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