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大戰略》
- 聯經
- Feb 5, 2021
- 13 min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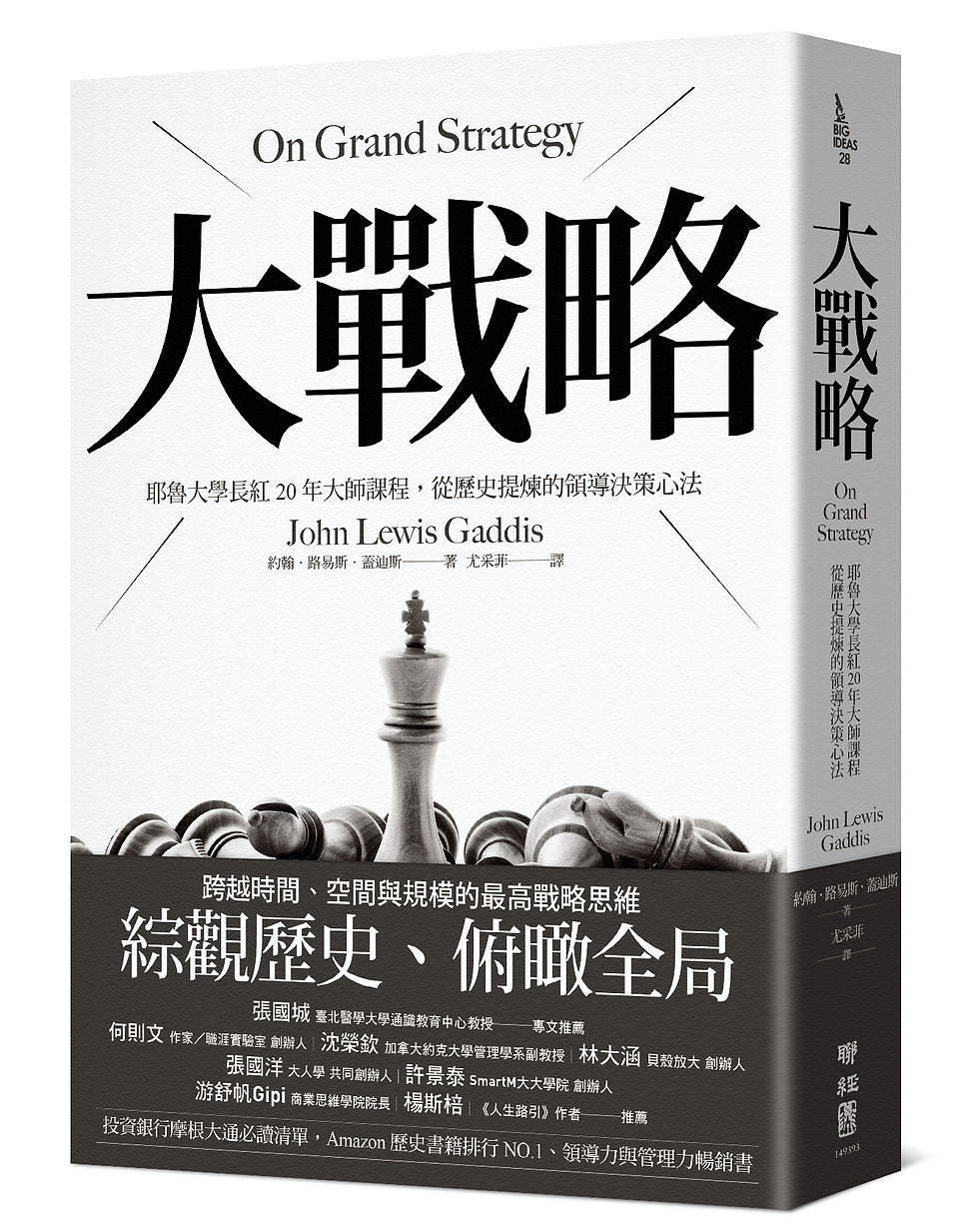
第七章
最偉大的戰略家
《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描寫到波羅的諾戰役要發生之前,安插了一個奇怪的段落(理查.佩威爾〔Richard Pevear〕和萊莉莎.瓦洛孔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的譯本頁七七四),兩位中心人物皮埃爾.別素豪夫(Pierre Bezukhov)和安德烈.博爾孔斯基(Andrei Bolkonsky)步出遮棚,抬起頭來,看到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與另一名軍官策馬經過。其中一人說:「戰爭的範圍務必是要擴大了,這種觀念我實在無法真心贊同。」另一位同意他的看法,說:「因為目標是要消耗敵人,這樣,就無法考慮到私人的損害了。」安德烈聽到這話很氣憤,因為俄法戰爭已經在他的莊園所在的土地上打了好久。他尖刻的向皮埃爾說道:「這些日耳曼人的腦袋裡永遠只想著他們的理論,真正有思想的人才不屑一顧……他們已把整個歐洲讓給了他(指拿破崙),然後現在要來這裡教訓我們了。真是好老師啊!」
在一段短短的距離裡面,托爾斯泰呈現了乘坐於馬背上和站立地上的兩種視角,讓讀者看到「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這是托爾斯泰多次以微觀事件來呈現宏觀意義其中的一次,這也是克勞塞維茨在他的著作慣常使用的手法。很少有人像那位馬背上的軍士和另外一位描寫他的小說家一樣,會在時間、空間、規模的問題上有如此深入的思考和寫作。
皮埃爾和安德烈在波羅的諾的景象,當然只是托爾斯泰的想像,不過克勞塞維茨是真的上過波羅的諾戰場。當法國於一八一二年揮軍入侵,他便辭去他在普魯士軍隊的官銜轉而投效俄軍,加入這場大戰。生性嚴謹的托爾斯泰於一八六○年代著手寫作《戰爭與和平》,應該是知道這件事的,他應該也已讀過克勞塞維茨過世後才於一八三二年問世的《戰爭論》。他筆下的克勞塞維茨偏好抽象觀點勝過實地觀察,直至二十世紀仍舊有很多評論家提出這樣的批評。有可能托爾斯泰這樣寫並不是在批評克勞塞維茨,而是想要呈現當時俄國人是怎麼樣看待他們新結交的普魯士盟友。托爾斯泰和克勞塞維茨不只是對於戰爭的實踐具有類似的看法,他們都借用了他們自己的軍旅經歷,建立了理論本身有其局限的理論。
克勞塞維茨VS.托爾斯泰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寫道:「讓我們陪同一個初次打仗的人上戰場吧!」這句話的語氣顯示他非常了解他所要講述的主題:
當我們向戰場接近時,隆隆的槍砲聲愈來愈響亮,夾雜著砲彈的呼嘯,這將開始吸引他的注意。砲彈開始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急忙跑上斜坡,奔向司令官及其隨從駐紮的所在。在這裡,砲彈和彈殼漫天飛舞,有關生命的嚴肅問題開始讓這位年輕人感到真切。忽然間,你認識的某人受傷了,接著一顆砲彈落在人群中間。你注意到有些人開始騷動,你自己也不再像先前那般沉穩鎮定,就連最勇敢的人都顯得有些心神不寧。現在,我們再往前進入戰場,加入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師團,激烈的戰鬥場面在眼前壯觀展開。砲彈有如冰雹般落下,我方的砲火也加入現場的轟鳴。我們再往前到旅長身旁,這位大家公認極有膽量的軍人,小心翼翼的躲在一片土丘、房舍或樹叢後面尋求掩蔽。一陣巨響,清楚的顯示危險愈來愈加劇。葡萄彈紛紛落在屋頂和地上,砲彈從四面八方飛過,槍彈在我們身邊呼嘯。再往前走,來到火線上,步兵隊在此以頑強不屈的精神已經堅守了好幾個小時。滿天飛舞著嘶嘶作響的子彈,如果子彈近距離擦過,聽起來就像是尖銳的爆裂聲。給人的最後一擊,就是眼看著人們陣亡倒下只剩殘缺的肢體,這樣的景象使人心臟噗通跳動,不由感到畏懼和悲傷。
新手在接觸到上述層層加劇的危險時,無法不意識到,在這個地方,人的思緒是受到其他因素掌控的,理性之光的折射運動與尋常我們在學院裡所做的臆測活動大不相同。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托爾斯泰所描述的波羅的諾戰役。托爾斯泰本人曾加入俄軍,在一八五○年代於高加索山、巴爾幹、克里米亞等地打過仗:
他所派出去的侍從官,以及駕下各元帥派來的傳令官,不斷的從戰場上傳回戰情快報。可是這些報告都是虛報,因為戰鬥熾烈,不可能說得出在某個既定時刻發生了什麼事;也因為那些侍從官並沒有到達實際戰鬥的地點,根本只是把從別人那裡聽到的話複誦一遍;又因為當一名侍從官騎了若干英里的馬回到拿破崙那裡時,戰況已經起了變化,所帶回的消息也已經不準確了……拿破崙就依據這些不可避免的錯誤消息下命令,這些命令要不是他下達以前就已經執行過了,不然就是沒有執行、不能執行。
法軍的將帥雖然距離戰場比較近,但也像拿破崙一般沒有實際參與戰鬥,只不過偶爾騎入步槍射程以內,沒有向拿破崙請示便自行下達命令,指示從什麼地方、朝什麼方向射擊,騎兵該往哪裡奔,步兵要往哪裡跑。即便如此,他們的命令也像拿破崙的命令一般鮮少得到執行。大部分時候結果卻恰恰與他們所吩咐的相反。士兵奉令往前推進,遭遇到霰彈攻擊便往回退後。雖奉命在原地待命,突然見到俄軍出乎意料的出現在眼前,不是掉頭就跑,就是往前衝。騎兵沒有得到命令,便逕自去追趕潰逃的俄軍。……只要他們離了槍砲和子彈的射程以外,位於後方的上級長官,便立刻重新整隊,要求他們恢復紀律,而在那種紀律的影響下,他們再度回到火網。在那裡,出於對死亡的恐懼,他們再次喪失了紀律,大群的盲目奔逃。
這些段落可以說是再真實不過了。不過,讀這些段落恐怕真的讓讀者覺得,這場戰役實在是一團混亂。除了沒有一個很確定的贏家以外,波羅的諾戰役其實締造了不少成果。
這場戰役拖垮了兩方的實力,然而俄國的幅員遼闊,如果俄方棄守莫斯科,他們甚至擁有比美國人還要廣大的空間可以撤退。法國人千里迢迢的遠征莫斯科,拿破崙無法抗拒拿下這座城市的念頭,希望能以此鎮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讓他前來求和。這位自凱撒以來最了不起的軍事天才一廂情願的認為狗的天性就是會去追趕車輛,而且一定會追得上,但當這個希望落空時,你會怎麼做呢?雖然在這個時候,他的士兵大可以提醒他,冬天很快就要來臨。
克勞塞維茨將這個時刻稱為拿破崙的「轉折點」,意思是法國人是自己打敗自己,因為他們將自己拖垮。「亮出報仇之劍」,俄軍現在有辦法將他們從鄉下趕回去。托爾斯泰筆下那位年老體胖又行動緩慢的總司令米亥爾.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對這一點的詮釋比克勞塞維茨好,很少有歷史人物出來露面不是想做些什麼事,卻意外達到更好的效果。拿破崙的軍隊傷亡慘重,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他連皇位也丟了。然而俄國沙皇卻以勝利之姿蒞臨巴黎,在倫敦受到高規格的接待,甚至還在牛津(Oxford)的瑞德克利夫之家(Radcliffe Camera)用餐,其他的賓客只能在陽臺呆呆的盯著這幕光景。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寫道:「戰爭的道理或許自成一格,但邏輯是共通的。」如果能藉助訓練、紀律和優秀的領導力,軍隊能夠暫時擺脫人會逃離危險的本能,從前面克氏關於初上戰場的新手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戰鬥是違反常識的。不過,隨著時間累積,邏輯終究能圍繞著道理而建立,從而使之變得模糊並加以取代。英雄主義只會耗盡你的精力。當補給線拉長,攻勢就會變緩,撤退還會引得敵人加以回擊。俄羅斯國土廣大,冬季寒冷。追逐車輛的狗從不知道追上了要能幹嘛。為什麼連最愚蠢的人都會記得的事情,卻遭到拿破崙遺忘了呢?
或許常識真的就像氧氣一樣,爬得愈高愈稀薄。每一次勝利都掩蓋了前一次的教訓,拿破崙把他自己的道理當成他的邏輯。就跟凱撒一樣,拿破崙的聲勢衝破了天,使得他不再能看清楚事情的基礎。像他們那樣的飛黃騰達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就跟那個年代剛升上天的熱氣球一樣,但地心引力並非不存在。
《戰爭論》VS.《戰爭與和平》
克勞塞維茨死於一八三一年,他死前《戰爭論》還未完結,因而留給我們一部內容有諸多矛盾的龐然巨著,我警告我的學生,如果過於細心研讀這本書,可能會使自己迷惘不已,腦中充滿問號,無法肯定他到底在講什麼,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誰。托爾斯泰則是在一八六八年完成《戰爭與和平》,但是他也說不清楚他寫這本書是實現了什麼:「這不是一本小說,算不上是史詩,也不是編年史。《戰爭與和平》是作者想要且能夠述說而出的成果,按著它被述說的樣子寫了出來。」以撒.柏林察覺他的閃爍其詞其實是種「折磨人的內在衝突」,存在於「自由意志的虛妄經驗」和「歷史決定論不可避免的現實」之間,這是否跟過於細讀克氏著作的結果很相似呢?
但要是克勞塞維茨和托爾斯泰是刻意要與矛盾搏鬥(恐怕還是自行引戰),而不是真的厭惡這些矛盾呢?他們兩人都將決定論視為法則,不可能會有任何例外。托爾斯泰曾寫道:「如果千百年中在茫茫人海裡,當真有一個人能夠按著自由意志行動,則這個人的一件與法則相反的自由行動,就會摧毀了全人類之存在具有法則可依存的可能性。」克勞塞維茨同意這一點,前提是法則必須容許「這個真實世界具有的多樣性」,則「當原則付諸於應用,做判斷時就能容許更寬廣的自由空間」。這句話說的是「任何規則的例外」,而不是「任何法則的例外」,意味著當抽象的概念接近現實,能夠帶來「更加自由的詮釋」。這一點跟托爾斯泰一致,他在這個層面上尋求推翻所有法則。
克勞塞維茨感到不滿的是,有太多理論太刻意想要成為法則。他引用了一個範例,這是普魯士人關於撲滅火災的規定:
如果一幢房子著了火,人們必然首先想到去防護位於左邊的房子的右牆,以及位於右邊的房子的左牆。原因在於,如果人們想要防護位於左邊的房子的左牆,那麼這幢房子的右牆位於左牆的右邊,因而火也在這面牆和右牆的右邊(我們已假定房子位於火災的左邊),這幢房子的右牆比左牆離火更近,如果不先在火燒到受到防護的左牆之前,先對右牆加以防護,則右牆很可能會燒毀。因此可以得到結論,未加防護的物品很有可能被燒毀,而且有可能會在另外一件未受防護的物品之前被燒毀。所以,人們應該放棄後者先防護前者,為了使人牢記這一點,只要記住:如果房子位於火的右邊,就要防護左牆,如果房子位於火的左邊,就要防護右牆。
克勞塞維茨答應他的讀者,《戰爭論》不會花篇幅講這種廢話,而是「把自己對戰爭經過多年思考而獲得的想法,與許多了解戰爭的能人之士的交往和從自己的經驗而得到的觀念」獻給讀者,這些,他會將之「煉製成純質的金屬小顆粒」,講給讀者聽。
這段話聽起來跟馬基維利好像,馬基維利是克氏熟知且崇拜的對象。不過,克勞塞維茨在五十一歲時死於霍亂,使他沒機會縮短《戰爭論》的篇幅並把他的要旨講得清楚一點。這本書並不像純質的金屬小顆粒,而比較像是一堆八腳章魚纏在沉甸甸的漁網裡。所以,就跟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樣,略讀此書得到的益處還大一些,你一定不想變得像邁可.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給克勞塞維茨的評語一樣,讀他的書卻陷入「令人火冒三丈的毫無條理」當中。
要略讀《戰爭與和平》比較難一些,因為托爾斯泰的文筆實在引人入勝。不過就算是這樣,這本書快要到結尾的部分,托爾斯泰還是花了長篇大論談論他的英雄無用論和歷史是多麼了無意義來折磨讀者。所以,最好還是先讓他的文字長河攜帶著你漂流過他的獨斷主張,之後再來重遊舊地就好。這裡來舉個例子,來看看托爾斯泰對於近代歐洲史的「理論」:
法王路易十四是個極其驕傲、專橫自大的人。他養著某某情婦,又有某某大臣,他的統治糟糕透頂。在路易十四之後繼位的人都昏庸無能,他們治理法國也都朝綱不振。他們同樣也有著某某寵臣、某某情婦。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一些人著書立說。到了十八世紀末,有幾十個人在巴黎聚集,開始談論起所有人都擁有自由、平等。因為這樣,法國全境的人開始相互殘殺。這些人殺害了國王和許多其他的人。就在此刻,法國出現了一位天才,他是拿破崙。他在每一處地方打敗了每一個人,也就是說,他殺了很多人,原因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然後為了某種原因,他接著去殺非洲人,殺得如此順利、如此狡詐,又如此精明,因此當他回到法國時,便命令人人服從於他,而人們也都照辦了。拿破崙成了皇帝,他又啟程到外國去,在義大利、奧地利、普魯士等地殺人,殺了好多的人。這時俄國有一位皇帝亞歷山大,決定要恢復歐洲的秩序,於是便和拿破崙開戰。可是到了一八○七年,他突然和拿破崙恢復友好,但到了一八一一年,他們又發生爭吵,又開始殺了很多人。拿破崙就率領六十萬大軍進攻俄國,攻占莫斯科,然而他倉促逃離莫斯科,俄皇亞歷山大……把歐洲團結起來,讓大家拿起武器對抗破壞和平的人。拿破崙所有的盟友一下子成了他的敵人,揮軍直搗他所組成的新軍。各國盟邦擊敗了拿破崙,進入巴黎,將他放逐到厄爾巴島(Elba),卻沒有剝奪他身為皇帝的尊嚴,在各方面仍舊恭敬待他,儘管在五年前和一年之後,人們都將他看成是土匪和非法之徒。路易十八因此登基執政,不過他卻是法國人和盟邦所笑話的對象……手腕很高的政治家與外交家在維也納舉行會談,這些會談使得幾家歡樂幾家愁。忽然間,外交家和君主起了齟齬,幾乎到了只要一聲令下就要發動大軍彼此屠殺的程度。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拿破崙率領一個軍團抵達法國,先前非常憎恨他的法國人又立刻向他臣服。盟國君主對此震怒不已,再度和法國開戰。他們把天才拿破崙打敗,瞬間將他貶為土匪,把他放逐至聖赫勒拿島(St. Helena)。這次的放逐,使他遠離他所心愛的人和他所熱愛的法國,在那塊岩石島嶼上緩慢進入死亡,將他的不世功勳遺贈給後代子孫。至於在歐洲,反動發生了,各國君王又開始對他們的子民放肆起來。
我們通常不認為托爾斯泰或克勞塞維茨是愛嘲笑人的人,然而這兩位均能夠奚落理論,這表示他們重視不符常規之事,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想要掩蓋這種事情的衝動。
我認為真正使他們著迷的是「反諷」(irony),這個字在字典裡的定義是「事件出現與先前預料相反的結果」。活在拿破崙時代的歐洲人不可能對其事蹟毫不驚嘆。這種驚嘆在托爾斯泰和克勞塞維茨心中縈繞不去,就像他們見證了與宇宙法則相斥的事件和人類一再出現的特質後所確信的想法(宇宙法則就是說目的可以是無限,然而手段卻永遠是有限的),對於像拿破崙這樣的人物而言,赫勒斯滂是注定要讓他跨越過去的。
戰爭的本質
到了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時候,拿破崙已經跨越了相當多障礙,先是尼曼河(Niemen),然後是受法國勢力籠罩的華沙公國(Duchy of Warsaw)和俄帝國之間的邊界,這些都不怎麼讓他掛心。拿破崙的「大軍團」(Grande Arme)除了有超過六十萬名將士以外(比薛西斯一世的人馬還多),還帶了三支浮橋,不過他們還是花了五天的時間讓每一個人渡河。然而當法軍十二月返回的時候,他們只剩下九萬人。看到這樣的折損率,不禁讓我們想要再次提起這個下列各起事件發生時(當波斯人攻打希臘、雅典人攻打西西里、羅馬人進入條頓堡森林、西班牙人嘗試跨越英吉利海峽,還有當英國人攻打進入美洲殖民地)屢屢問過的問題:他們的腦子裡到底在想些什麼?或者,換種方式問,拿破崙是遺忘了什麼?
克勞塞維茨對於這個問題有著敏銳的見解,但我們得要去刨根究底的從他的長篇大論中把答案挖出來,就像奧古斯丁對於正義的戰爭的看法一樣。《戰爭論》的一開頭,可比巴頓將軍(Patton)在以他為名的電影《巴頓將軍》的開頭,大聲的訓斥他的軍隊一般:
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隨著暴力同時存在的,是一些自我加諸、難以察覺的限制,也就是人們所知的國際法和慣例,這些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實質上並不會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質暴力,因精神暴力除了敘述於國家和法的概念以外並不存在,所以這是一種戰爭的手段,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敵人是其目的。
但接著作者提到這個條件:「理論上,那是戰爭真正的目的」,則其實踐應該為何?「暴力的充分使用絕不排斥智慧同時發揮作用」,克氏如此斷言,「如果文明的民族不殺俘虜,不破壞城市和鄉村,那是因為他們在戰爭的手段中大量的應用了智慧,讓他們學會使用比粗野的靠本能來發洩還更有效的使用暴力的方法」。讀到這裡,讀者開始昏頭了,可是我們才讀到這本厚書的第二頁而已呢。無論你對巴頓將軍有什麼看法,至少他的話比較容易聽得懂。
他是在訓誡他的軍隊要思考些什麼,但是克勞塞維茨是要教我們如何思考。他很肯定一件事,如果不先掌握事物最純粹的形式,我們無法了解任何事情。這個概念出自柏拉圖,但近代最極力提倡的人物,應屬幾乎與克勞塞維茨同一年代的哲學家康德,他主張要先將對立相反的論點完整呈現,才有辦法使之調和一致。漸進式的變化、條件的符合及對立的消減才會跟著出現。或者,就像克氏自己解釋的:
當兩個概念在邏輯上形成真正的對立,……基本上兩者之意義已互相暗示於彼此之間。然而如果我們智力上的限度使我們無法同時了解兩者,並透過此對立在其中一個概念裡去了解另一概念的全貌,則兩者中之任何一者皆無法為我們闡明另一者概念當中的許多細節。
這裡講的方法不適合缺乏想像力的人,他們一下子就會搞糊塗,也不適合怯懦之士,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太過於震撼。如果克勞塞維茨的目的,像維吉爾給但丁提供了很多靈感那樣,是要帶領我們通過地獄,則這個方法雖令人膽寒,卻正是恰到好處。
作者為耶魯大學教授,冷戰史研究權威,曾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ΦΒΚ會(Phi Beta Kappa)教學獎章,著作豐富,著有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等,其中《喬治•肯楠傳》(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獲2012普立茲獎傳記文學獎。
書名:《大戰略》
作者:約翰.路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