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一場華麗的獻祭之後
- 祝平一
- Dec 29, 2020
- 4 min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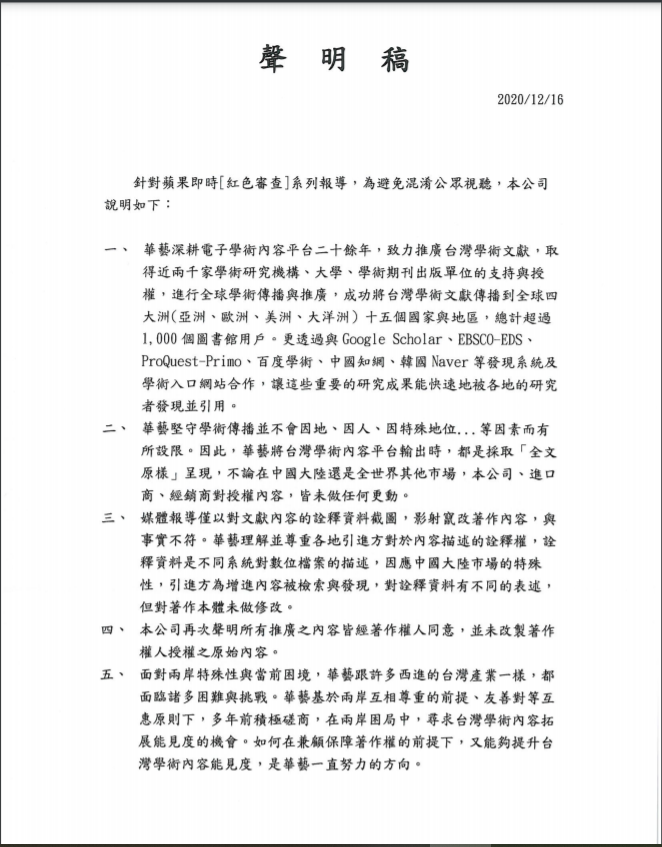
圖片來源:華藝線上圖書館網站
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這篇名著中,作者死於作品送達讀者之際。作者不再擁有作品的宰制權,是讀者的詮釋使作品成為意義開放的存在。在羅蘭.巴特筆下死去的作者還算幸運,如果是在華藝的手上,某些台灣作者的作品在還沒有送到中國讀者眼前,便已然凋萎:這是一場以「台灣」、「作者」為犧牲的華麗獻祭。
華藝是台灣最大的學術資料庫。它在中國成立「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卻竄改論文的後台資訊(metadata),封鎖某些論文,以合於中國意識形態的管制。中央大學教授副教授皮國立,只因名字有「國立」二字,被剝到只剩一層「皮」,成為年末學界最令人帶淚的笑話。事發之後,舉國譁然。華藝第一時間卻反控媒體報導「與事實不符」,並謂「任何授權華藝資料庫之著作權人,若不願意該著作在海外推廣,可與本公司聯絡;本公司接獲書面通知後,可安排代理商將該著作在特定市場不予呈現。」一副願者上鈎的霸氣。後經社會學界抗議,才放下身段,在自己的網頁上發了道歉聲明。
在這場祭典中,華藝竟發揮了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筆下部分的「作者功能」。作者成為文本的分類標簽,使得作者和作品成為權力宰制的對象。作者雖然存在,有的被消失了,有的被改名了;作品必須符合中國的論述規則,才能成為學術論域中的陳述。華藝儼然成為陳述准入與排除的介面,恍如中國國家權力的監視器。
自上世界末以來,學術資料庫已成為全球學界難下之虎。在網路時代,訊息就是金錢。學術資料庫看準這一點,透過期刊收集學者授權,成為寡占學術訊息的通路,因而索價不菲。不是財力雄厚的國家或學術機構,難以負擔;而學者欠缺了資料庫,便難以及時跟上與自己領域相關的研究。許多學術資料庫還提供了各種統計數據,無形中成為學界定義聲望的標的;而學者的研究成果若無法在資料庫被檢索到,便仿佛消失於無形。
商業資料庫的運作奠基於信任:作者信任期刊而授權;期刊則信任資料庫能為作者和作品服務,使之成為公共資源,提供便利的檢索,讓讀者能迅捷地找到所需的資料,而與之合作。信任在資料庫行業中尚有另一層意義。無論內容的提供者或是使用者,相對於寡占通路的學術資料庫平台,都是弱勢。作者與讀者無法得知資料庫平台如何處理他們所授權的作品或是正在閱讀的資料。
因此,作者的授權完全是基於信任期刊和資料庫。資料庫業者的收益,則來自與期刊、作者、讀者間的互信;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如實地登錄所授權的資料,包括作者的服務單位、作品的標題和關鍵詞。因為這些元素,正是讀者搜尋所需的指引,也是作者呈現自己的期待。
然而,華藝卻辯稱:「本公司……並未改製著作權人授權之原始內容。」它只是「理解並尊重各地引進方對於內容描述的詮釋權,……對詮釋資料有不同的表述。」魚目混珠地將後台資訊稱為「詮釋資料」。誠如社會學界所指出,華藝此舉違反著作權法第十七條,「已嚴重侵害授權機構與作者之權益」。
中國一直利用市場准入,以商業推銷中共意識形態,而引發目前全世界與中國貿易紛爭。不意華藝竟一心配合,自我審查,罔顧著作人與授權單位的權益。華藝既已背叛了作者、期刊與讀者間默會的信任,除了譴責之外,拒絕再授權華藝是國內各期刊與作者唯一的選擇。因為華藝即使自承有失,其在中國所建立的分身資料庫,日後會如何處理資訊,作者仍然難知。既然難以互信,唯有撤回授權。教育部也應提供權益受損的機構和作者所需的法律救濟。
華藝事件也讓我們省思台灣學術資料庫商業化的問題。台灣真的需要商業電子期刊的平台來推廣學者的研究嗎?為何電子期刊的服務不能是國家圖書館公共性服務的一部分嗎?如此提問,主要是因為台灣大多數學術論文的生產者倚靠的是國家的經費,亦即納稅人的錢,為公家建立開放的資料庫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礎。以國家之力,建置公共的學術資料庫,回饋給社會,推廣給全世界;以學術研究貢獻,行銷台灣之小國好民,孰曰不宜﹖
國家圖書館目前已提供博碩士論文的授權平台,供登錄者無償取用,這或許也能推廣到一般期刊授權;甚至能將台灣學者以外文發表的論文都收入,建置「台灣學術資料庫」,在這場華麗的祭儀之後,挽救台灣作者之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