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後疫情效應》
- 天下文化
- Mar 26, 2021
- 11 min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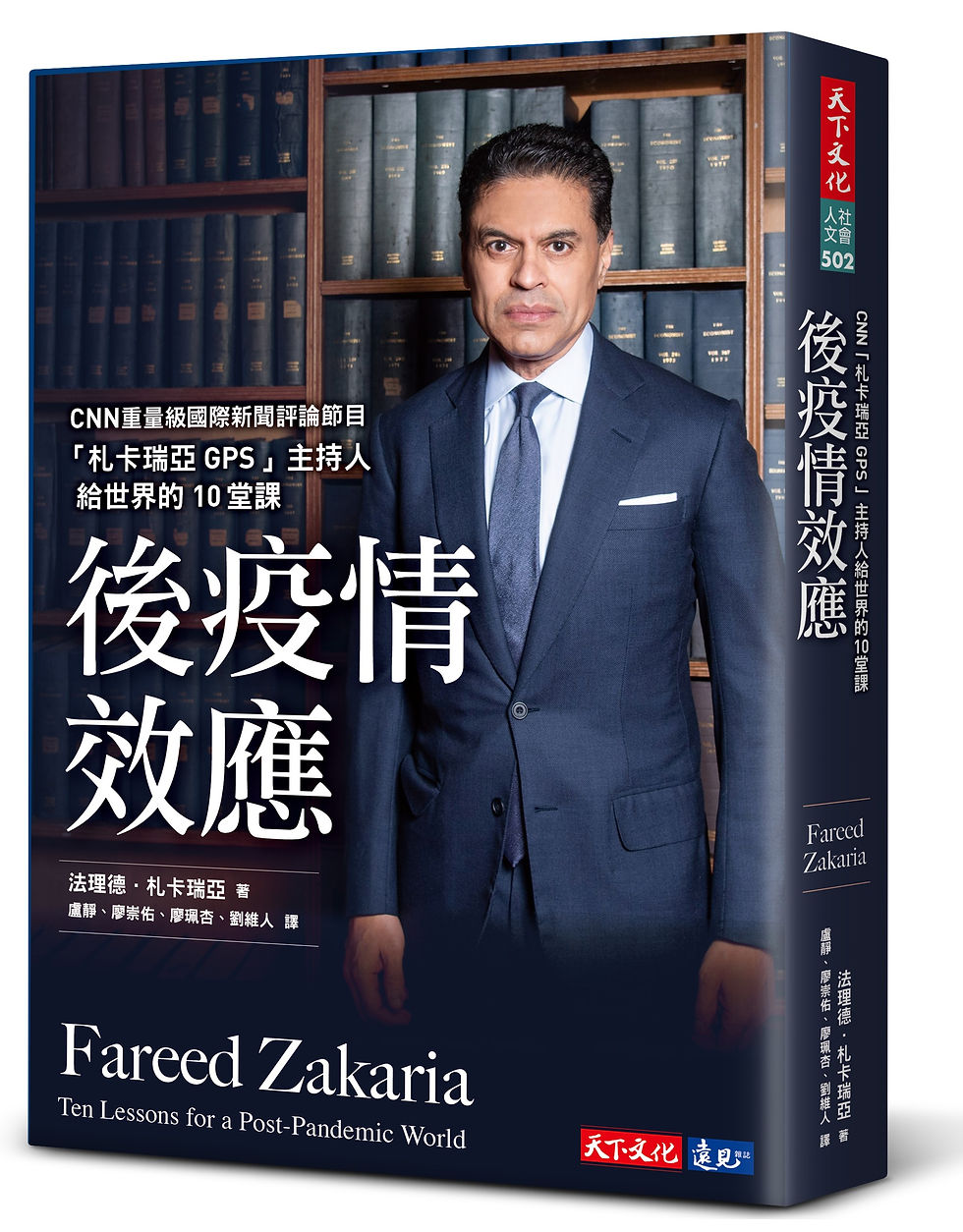
第4課 大眾應遵從專家建議,專家應傾聽大眾意見
二○一六年,當川普即將獲得共和黨提名時,有人問他的外交政策都是向哪些專家進行諮詢。他回答:「我第一個諮詢的就是我自己,因為我的頭腦很好。我的首席顧問就是我,我對這種事的直覺很準。」後來,他解釋了自己為何不依靠專家。他說:「專家很糟糕。你看現在有這些專家,還不是一團亂。」幾個月後,英國政治家戈夫(Michael Gove)因為主張離開歐盟對英國企業比較有利而支持脫歐。他在遭到質問時,被要求舉出有哪些經濟學專家支持他的論點,但他卻回答:「英國人已經受夠專家了。」
現在,由於全球都受到二○一九冠狀病毒大流行所影響,人類應該要清楚知道,我們必須聽從專家的意見才對。但事實上,並非每個國家都是如此。許多東亞國家的人民天生就非常尊重權威,尤其是科學方面的權威。臺灣的防疫措施在副總統的指揮下,可說是近乎完美。這位副總統具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是一位流行病學專家,他還曾經以衛生署署長的身分,帶領臺灣度過SARS疫情。德國在曾經是科學家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帶領下,採取了許多謹慎且以事實為基礎的防疫措施。當希臘總理被問到為何希臘能夠成功遏止疫情擴散時,他回答:「因為我們聽從專家的指示。」
然而也有些國家初期尊重專家,卻在日後開始質疑醫療專業人員的建議,甚至拒絕配合防疫措施。例如在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就鼓舞了這種態度。波索納洛認為二○一九冠狀病毒只是「小感冒」,並抨擊醫學專家對於減緩大流行的建議。他不但開除了一名衛生部長,還讓後續的接班人辭職。雖然政府規定要戴口罩,他還是拒絕配合,最後在一位巴西法官的命令下才戴上口罩。結果,波索納洛成為自己草率態度的受害者:他在二○二○年七月宣布,他的二○一九冠狀病毒篩檢出現了陽性反應。強森在疫情爆發初期,顯然未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最終因為染上二○一九冠狀病毒而住進加護病房。在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鼓勵民眾外出、參加集會、握手和擁抱,但這些行為與公共衛生官員的建議完全相反。歐布拉多鼓勵墨西哥人繼續過一般生活,並保持樂觀和好心情,彷彿正能量可以抵禦二○一九冠狀病毒。雖然有專家警告,如果沒有良好的篩檢和戴口罩的規定,感染的情形將會迅速傳播,但美國的一些州長仍堅持重新完全開放各州。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支持右派的運動,「解放」受民主黨州長暴政統治所苦的州,因為這些州正在實施封城。然而,這些封鎖措施正是川普政府所建議的做法。事實上,川普不斷在違反自己的專家所給的建議。他好幾個月以來都拒絕在公共場合戴口罩,表示只有脆弱的自由主義者才需要把臉遮起來。他向民眾推薦自己的可疑療法,而這些方法大部分都直接牴觸美國政府公共衛生官員的建議。他甚至暗示可以喝下清潔用品,讓來舒(Lysol)的製造商不得不警告顧客,千萬別喝漂白劑。川普還宣揚瘧疾藥物奎寧(hydroxychloroquine)的療效,宣稱這款藥物能夠「逆轉情勢」,並於二○二○年五月宣布自己已經服用了一個多星期。雖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警告奎寧可能會引發致命性的心律不整,但川普表示:「我感覺很好。就是這樣。只是一種感覺。你知道,我是個聰明人。我感覺很好。」這件事有如真實人生在模仿藝術作品,呼應了喜劇演員荷伯(Stephen Colbert)在《荷伯報告》(The Colbert Report)第一集中所提到的感實性(truthiness)的概念。節目中的角色問道:「《大英百科全書》憑什麼對我說巴拿馬運河是在一九一四年完工?如果我想要說這發生在一九四一年,那是我的權利。我不相信書籍,書裡都是事實,但沒有心……面對現實,各位,我們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分成了以頭腦思考的人和靠直覺行動的人……各位先生女士,真相的源頭,就是直覺。」
到底科學是什麼
這些人的行為,簡直是在體現恐怖的無知主義。對於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解決方法似乎很明顯:按照科學的建議就對了。但是,我們到底可以透過科學知道什麼?美國政府傳染病專家弗契博士(Dr. Anthony Fauci)最初對二○一九冠狀病毒的危害採取了冷處理的態度。他在一月下旬曾表示:「美國的風險非常非常低……美國民眾不必擔心或害怕。」幾天後,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薩爾(Alex Azar)也表示,政府的公共衛生官員普遍認為「美國人受到感染的風險依舊很低」。這說法呼應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結論。世界衛生組織直到一月底之前,都低估了疫情演變成大流行的機率。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最初建議民眾待在室內且不用戴口罩,卻在幾個月後改變決定,呼籲民眾做相反的事。有些國家徹底實施外出限制,其他一些國家則根據自己的流行病學專家和模型,決定不實施封城。我們該如何看待這類情況?
事實上,在面對像是二○一九冠狀病毒疫情這樣的重大問題時,科學沒辦法直接帶來一個簡單的答案。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弗契在得到初步證據後,做出了合理的結論。許多科學家最初都認為冠狀病毒不會造成重大危害,但每個人都是在資訊極少的情況下做出快速判斷。二○一九冠狀病毒就是一種新型的病毒,我們至今仍不清楚其傳播率和殺傷力。當證據出現改變,弗契等人也開始改變想法。這很正常。專家不是全知全能。某些早期的模型對感染二○一九冠狀病毒的住院率做出了過高的預測,導致醫院為了空出床位而停止進行非緊急照護。這麼做似乎讓許多非二○一九冠狀病毒患者的病人誤以為自己就算去了急診室也不會得到照應,而且會擔心在人擠人的醫院中感染到二○一九冠狀病毒。某些醫院的系統顯示,心臟病的患者減少了五○%,表示許多人可能是默默在家中病逝,但他們原本可能有機會得救。後來估計的住院率,則愈來愈準確。
我們總認為科學能夠帶來一個絕對的答案,但這並不是科學真正的運作方式。首先,科學是一種探究方法,一種提出問題並嚴格檢驗這些假說的過程。有了更新、更好的資料後,才能夠得出更新、更好的結論。科學家對於二○一九冠狀病毒仍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科學家終究會找出答案,但往往不是幾個月內就能做到,而是要好幾年。在某些研究領域(例如氣候變遷),專家必須耗費數十年進行研究、收集大量資料、發表許多經過同儕審查的研究文獻,最後才能達成共識。儘管如此,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初步共識,日後很有可能會被修正或甚至被徹底推翻。我們在學校學到的科學知識,大部分都是普遍受到認同的共識。
二○一九冠狀病毒則完全不同。當弗契等公共衛生官員必須立刻決定要以多嚴肅的態度面對疫情時,二○一九冠狀病毒只出現不到兩個月,而且只在少數幾個國家中爆發。不到數週,更多相關資訊開始不斷出現,現在每個月還會出現各種相關研究。但是在疫情爆發初期,醫生和科學家就像戰場上的將軍一樣,只能獲得不完整且往往是錯誤的資訊。更糟糕的是,他們也明白這一點。然而,他們必須遠在情況尚未明朗之前,就做出非常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決定。
在撲朔迷離的情況下指揮防疫,通常會陷入兩難。在危機初期,有些科學家覺得應該要把疫情描述得比目前證據顯示的情況更嚴重。這方法有時候是為了鼓勵民眾認真看待專家所頒布的準則。這種方法或許具有短期好處,但長期下來會有一個嚴重的風險。若事實證明預測失準,或是出現改變現狀的新資料時,就會全面損害到專家和科學的權威與誠實性。過去的流行病就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舉例而言,弗格森(Neil Ferguson)是一位流行病學家,他所提出的預測模型是讓英國決定實施外出限制的基礎。弗格森在二○○九年時,曾經預測豬流感可能會在英國導致六萬五千人死亡,讓當時擔任倫敦市長的強森等政客感到恐慌。最後大約有四百五十名英國人死於H1N1病毒。但錯誤的預測模型已經造成了損失。十年後,當強森擔任總理時,可能由於當年過度恐慌的記憶猶新,導致他對二○一九冠狀病毒的疫情反應不及。現在,其他不想聽專家意見的政治人物會四處引述各種說詞,或是拔擢自己的「專家」,藉此為自己希望採取的行動進行背書。
既然如此,對真正的專家來說,最好的做法是什麼?答案是:讓大眾理解到底何謂科學,也就是科學的原理。講到科學時,大部分美國人只會想到最終結果,也就是新發現、新突破或新發明。他們看見的是銀河系令人眼花撩亂的照片,讀到的是藥物奇蹟般的療效。然而,科學其實是一種學習和發現的過程,途中會充滿許多失敗和失望。哈佛大學的學者平克(Steven Pinker)在二○二○年四月的一次採訪中提出警告,科學家「努力而來的權威性」可能正在瓦解,許多民眾可能認為「穿著白袍的人,只不過是另一種牧師」。平克呼籲科學家應該要透過「公開辯論和拆穿流言」等方式,開始「向世人呈現科學的運作方式」。梅克爾宣布重新開放德國的計畫時,在全國播出的電視節目中為民眾上了一堂科學課。她解釋,二○一九冠狀病毒是以「一」的速度繁殖,表示每個感染者會在康復之前感染另一個人,因此不會增加被感染者的淨數目。這讓她對解除外出限制抱持謹慎而樂觀的態度。然而,德國目前正如履薄冰。若繁殖率提升至一.一或一.二,德國的醫療體系很快將不堪負荷,因而必須恢復封城。梅克爾讓大眾了解影響其決策的關鍵因素,而不只是靠嚴格實施封城來達到最佳結果。例如德國、南韓和臺灣等許多政府,都能夠以相對短暫或部分的封城及大規模的測試和追蹤,成功控制二○一九冠狀病毒疫情。
專家的態度是否真誠,民眾其實可以感覺到其中的細微差別。然而,菁英卻常對外行人抱持高姿態。許多證據顯示,東亞國家「全民戴口罩」的規定是成功控制疫情的關鍵,但西方專家一開始卻都忽略了這一點。即使目前仍未完全確定口罩的效力,但美國政府對於口罩的公開言論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官員極力反對使用口罩,聲稱口罩無法保護普通百姓,而且口罩應該留給醫生和護士使用。然而,如果這麼做的真正目的是要避免囤積醫用外科口罩,政府難道不能至少鼓勵民眾在家裡製作只需要一件上衣和剪刀就能完成的簡易布口罩嗎?美國衛生署長等官員後來承認,他們擔心民眾會出於恐慌而搶購並囤積口罩,讓醫生和護士口罩不足的問題更加惡化。顯然對他們來說,向民眾解釋「某些口罩應該留給醫護人員,一般人可以戴其他口罩」實在太過於困難了。
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數十年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曾在回憶錄中解釋,他為何在冷戰初期時,決定以「蘇聯企圖向全世界擴張」的說詞來恐嚇美國大眾。他的言詞中滿溢著高傲的態度:
唯有放棄修辭,選擇平鋪直敘,放棄華美之詞與細節,選擇以直白到近乎殘酷的文字解釋,才能順利傳達資訊……在國務院,我們常討論究竟傳說中的「一般美國公民」每天會花多少時間聆聽、閱讀和談論祖國以外的全球新聞。對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已有家室,並且在家中或在外工作的人來說,我們認為每天有十分鐘就已經是高平均的水準。假如這屬實,想要讓人理解的重點,就必須以非常清楚的方式表達。
艾奇遜深知對抗蘇聯問題的複雜性。但如他所說,當他和其他官員在以「比事實更清楚」的方式向民眾說明情況時,他們編出了一個美國的生存性和全球性的危機,這個危機從拉丁美洲到印度支那,來自世界各地,而且從政變到祕密戰爭,必須無所不用其極的面對這種威脅。細節愈多,流的血就愈少。
專家解釋得愈清楚愈好,虛偽的程度也會愈低。英國出現過兩個明顯的例子。二○二○年五月,弗格森被發現違反了隔離規定與自己的愛人會面,因此被迫辭職。後來在同一個月,民眾的憤怒變得更加強烈,因為有消息指出強森的首席顧問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的妻子確診二○一九冠狀病毒,但他卻無視居家隔離的規定,開車橫越英格蘭數百英里去探望家人。他辯稱自己是為了確保小兒子能夠獲得照顧而不得不採取行動,而總理也表態支持他。卡明斯拒絕下臺,但被要求犧牲家庭生活(錯過婚禮、嬰兒出生和喪禮)的英國人卻感到怒不可遏。在這些醜聞爆發之後,民眾對保守黨政府的信任度急遽下降,違反隔離的事件也頻頻傳出。
在大西洋兩側,專業知識更是遭到蓄意貶損。然而,川普對專家的愚蠢態度和他自己的無能,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可以解決廣泛的全國性問題,尤其是經濟封鎖讓數百萬人失業並讓公司破產後,必須試圖再次重新開放經濟等這類重大議題。科學資料很重要,但經濟分析也很重要。公共衛生官員不會知道各種經濟封鎖方法的成本和收益。在封鎖和開放大都會地區時,應該要諮詢的是都市計畫技師。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曾說過:「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他的意思是,戰爭不能只靠專業軍事知識,還必須整合其他觀點。現代的戰爭尤其如此,因為現代戰爭在本質上是「全面」的,會影響到社會的每個層面。學者柯恩(Eliot Cohen)表示,例如林肯、邱吉爾、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班-古里昂等在這類衝突中成功的領導人(我個人認為應該要再加上小羅斯福),是能夠質疑和否決將軍的意見、考量其他觀點和學科,並制定出全方位政治軍事戰略的人。
在大流行期間領導國家,與在戰爭期間領導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會對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影響。領導人通常必須犧牲可怕的代價,以一些風險代替另一些風險。也許這就是為何傳說中的戰時領導人之一克里蒙梭曾說過:「戰爭太重要了,不可任由將軍決定。」他的意思並不是可以在不靠將軍的情況下贏得戰爭,而是必須輔以其他類型的專家,才能盡可能全盤了解全局。基於這種精神,我們也可以說:大流行病很重要,不應該只交給科學家。科學家是不可或缺的成員,但其他領域的專家也是。
作者獲《前景》(Prospec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評選為「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票選為「過去十年十大全球思想家」(top ten global thinkers of the last decade)。
主持CNN重量級國際新聞評論節目《札卡瑞亞GPS》(Fareed Zakaria GPS),全世界各地有兩億兩百萬個家庭收看。為《華盛頓郵報》撰寫每週專欄,每月有八千萬至一億名讀者。
著有《自由的未來》、《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
《自由的未來》出版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評論道:「札卡瑞亞是極為傑出的年輕作家,他針對西方憲政原則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寫下一本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著作。」
《後美國世界》發表後,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說:「法理德.札卡瑞亞對國際時事的分析一直以來都很出色,但更難得的是,他都是對的。如今,他又出版了一部充滿洞見的傑作。」
書名:《後疫情效應》
作者: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時間:2021年2月5日










Comments